旧文新发第二弹。这篇散文是七校联合辅修写作课的作业,记录了当年和朋友寒假时去江汉路一带的所见所闻所感,原文写于2017年2月。今日天晴,又重走江汉路,逛武汉美术馆,享受周末的欢愉片刻。疫情好像已经结束,尽管地铁依旧提醒大家戴好口罩,路上还有一些未拆除的核酸亭,街边也还有许多倒闭后没有重新租出去而大门紧闭的门面,但步行街和小吃街的人流仍然昭示着这里也算得上武汉数一数二的繁华商圈,三年疫情留下的阴霾在人们的笑颜中一扫而空。回顾此文,想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六年前后无不同~
以下是原文——
去年年底,武汉六号线正式通车,中山大道和沿江大道一带也终于解除了所谓“蓝色警戒”——撤下了象征施工的蓝色围栏,因修地铁而“闭关”一年半的江汉路也终于重新对武汉市民敞开了怀抱。小时候,印象中汉口一带最繁华的地方大概就是江汉路了,吃喝玩乐,电影书城,我这个时常往外跑的闲人可以说是对这个地方还是有点感情。其实对不少的老武汉人来说,江汉路更是他们心中一座城市的中心。这不,一听说中山大道焕然一新,重新开放,寒假时就和朋友相约到那一块去扫街,重新找找童年时的记忆。
那天还是第一次乘坐地铁六号线,从钟家村到江汉路,大概二十分钟车程,中间穿过汉江。大概赶上了开年之后的第一个周一,车上的人不少,大多数上班族略显倦怠,或斜倚着补觉,或拿出手机刷刷新闻,像我们这样还算闲的人确实不多。朋友时不时理理挂单反的背带,寒暄中,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我们是在六渡桥站下的车,一出地铁站,迎接我们的是宽阔的人行道。我略显惊讶,和印象中很不同,当年的这条街,哪有这么宽阔的人行道。当年的人行道一边被占道经营的小贩占去大半,一边又被占道停的小车堵着,不像现在,两边的占道现象都没了不说,听朋友介绍,中间的公交车道也变成单行车道了。可能时候尚早,人还不多,两边商户大门紧闭。天也不甚晴朗,寒风穿过刺痛着脸颊,街上略显冷清与肃杀。但是这条往昔繁华的长街,依旧保持的他本应该有的尊容,只是现在略显安静。除了静,也很净。武汉虽说前年终于评上了全国文明城市,可是这么干净的街道也着实让人感到有种略带惊讶的赏心悦目。也许是对这座性格张扬的城市的“脏乱差”格外宽容,但依旧更爱他收敛任性,不卑不亢的样子。
一路交谈着,已经走到前进四路的路口。十字路口的那个大钟还没有停,时间还在一分一秒的过,与之相对的水塔静默矗立着,并未见衰老的容颜里也好似能听见对时间流逝的叹息声。水塔原是一个外地人来汉办水电公司时建的,作消防储水和之用,公司取名自《周易》的既济卦,水火之间,既济未济之间,其中蕴藏的宇宙哲理,也让水塔保存至今,成为江汉路的地标。现在水塔已经不作储水供水之用,化身成为介绍汉口江汉路历史的博物馆,在一代又一代武汉人的记忆里留下历史变迁与时代发展的烙痕。朋友不断调整角度和光圈,对着这座见证江汉路百年历史的地标按下了快门,我则在阅读相关介绍时神游,想象着那个年代的这座城。
再往前走不远便是佳丽广场、王府井百货和万达购物中心,童年记忆中吃喝玩乐看电影买零食的地方。商场的外体已经略显斑驳与黯淡,隐身于附近的高楼林立之中。地图上这些地方或许不是最突出的了,但是当时这里的繁华与新潮在武汉市都是有名有响的。我的注意力还是被商场对面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吸引,看样子是一个莫比乌斯带,扭曲的圆环只有一个面,好像是在用这神奇的拓扑几何来象征世上岂止有这一条路,有走不完的无穷无尽的路。出离神游之外,看见有几个小孩子穿着厚厚的棉衣在雕塑上施展着笨拙的拳脚,旁边的大人坐着谈天说地。再看看周围,恍然发现身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街上也热闹起来。有步履匆匆的上班族在赶着路,也有情侣手挽手笑着言语,我和朋友也继续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出现了一条岔路,岔路口中央是武汉美术馆,好像已作他用。由于是周一,闭馆整理未对我们开放,我们也未在这里作过多停留。主要是朋友对我说前面的吉庆街改了大面貌,叫我一定去好好看看。我记忆里的吉庆街还是那个大牌坊,白天的牌坊显得庄重,一到晚上,这里就是武汉人吃夜宵纵酒狂欢的地方。自从长江隧道建成之后,阻断了直接到吉庆街的交通,扎根于这里的武汉老味道“老通城豆皮”也一度销声匿迹。这次,令我意外的是,以前门庭冷落的吉庆街现在也可算是人流络绎不绝了。除了“老通城豆皮”、“德华楼年糕”等复苏的饮食文化,新建设的吉庆街融入了更多的民俗元素,打造出武汉民俗街的味道。写着武汉方言的旌旗在屋檐下飘着,转糖、名字花鸟画等各种充满民俗野趣的手艺人也在这里摆摊,还有曾有耳闻的泥人胡也在这里,用江滩边特有的红泥创作着属于他的艺术。我想,这样的复兴给吉庆街注入的活力,使它承载的已绝不仅仅是一个宵夜、听曲的排档夜市,而且是街头巷陌都能触及到的汉味文化的代表,这也许才是那个牌坊该承载的东西。
走过吉庆街,竟然已经快到了饭点。我和朋友却没有要吃点东西的意思,却一致决定要先去江滩走一遭再回来吃。穿过繁华之下窄小的里份和仅有一个方向的小路,直往江滩的方向走。汉口江滩也是童年常去的地方,春天喜欢折下江畔的杨柳枝条编作手环,夏天则偏好戏水和玩泥巴,秋天也许还能见着有人放风筝,像这次冬天去江滩怕是很少了。和朋友沿着江边走了几步,江风很狂,好像要把人吹得飞走了。我们于是退回来,在花坛后面走。时间在聊天中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就走到了江汉关和抗洪纪念碑。这是我真正想来看的地方。江汉关的钟声不知道还会不会敲响,看到它的时候它应该还是和百十年前刚落成一样挺拔。汉口的租界文化和码头文化从江汉关开始,散尽历史硝烟和屈辱岁月的阴霾之后,它的守望依旧让我们现代人在商业繁华的汉口,依稀听见不知道是不是由它发出的钟声。抗洪纪念碑上有毛主席的头像,小时候听祖辈人讲过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那一年武汉发生的特大洪水。由于对那件历史事件了解的不多,只知道这样的一个地标建筑也一直在那里,无声的向我们后辈人讲述着先辈人和这座城发生的故事与传奇。
我们开始往回走了,从步行街穿回江汉路的购物广场,准备吃点东西。江汉路步行街可算是闻名中国的步行街。地铁六号线在修的时候对步行街的正常开放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这里的现代潮流元素很丰富,是逛街很好的去处。步行街里也有那个年代遗留下来的洋式建筑,其实我觉得没多大看头,也许是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便也就没在这条老步行街做过多停留。吃过午饭后我们又往来时的地方走,走过六渡桥,走过统一街,走过三民路,一直走到汉正街。朋友从小在这里长大,她带我走街串巷的同时也在和我讲述着她眼里这里的变化。她说这一块倒是没怎么变,江汉路倒是变化真的大。我可能没她的体会深,却也深以为然。
一开始我就已经说到了,若问一个老武汉人,他眼中武汉的中心是哪里,他八成会说是江汉路。从地名我们就可以看出,江汉路取名长江汉水,地处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如果把长江和汉水比做成江城的主动脉,那江汉路在动脉中心,周边小路四通八达,却也似乎抵得上心脏的位置。这里曾经也许算是江城最繁华的地方之一,但也绝不是那天扫街我眼中的繁华。过去的江汉路在周末可以说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吸引人的都是商业街和购物广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弥漫着快餐文化味道的种种视听之娱和口腹之欲。水塔被人遗忘,浮雕被人忽略,各式各样的里弄隐藏于街市。是的,我童年印象里的江汉路好像很新潮,北京上海都有的大型购物广场、电影乐园还有美食基地我们这里都有,但是人们被这些东西去吸引好奇心和注意力的时候,真正代表武汉精神,蕴藏城市灵魂的那些历史故事和老建筑是不是就被淡忘了呢?我们记忆中老武汉的味道,是不是也在这样的一口辛辣的羹汤里慢慢淡化了呢?无疑是的。
而江汉路真的变了,变化很大。变得让来人不仅仅享受于商业繁华给人带来的感官刺激与消费快感,而是也让人愿意驻足水塔去回忆那段历史,让人更方便了解老汉口特有的里份式建筑,让人更容易找到武汉味道,这些激发的,是一个武汉人与这座城市精神层面的洇透灵魂的共鸣。城市在不断发展,也在不断繁荣。以江汉路为例,在经济繁荣之后,武汉也真正实现了文化繁荣与文化复兴。我想这种繁荣应该才是我和朋友那天扫街所见的繁荣。
其实,武汉这座城市也是一样,江汉路的变化只是这座城市变化的一个缩影。时代在发展,城市在繁荣,武汉确实也在完成属于自己的复兴。武汉这座城市已经渐渐在一种文化底蕴的沉淀下,慢慢脱去往日浮躁的外衣,真正能够以其自身的涵养与气质吐纳着时间给其带去的种种兴衰变迁,以最全新的姿态接受者一代又一代人的检阅。而我——在江城出生成长和求学,见证着武汉的变化,也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血脉里和这座城市密不可分的一点点联系,我想那就是面对这些城市历史文化的时候,对自己精神思想世界的那一点点塑造吧。
重走江汉路,也重新寻回这座城市给我的那些宝贵财富。
原文写于2017年2月,新发于2023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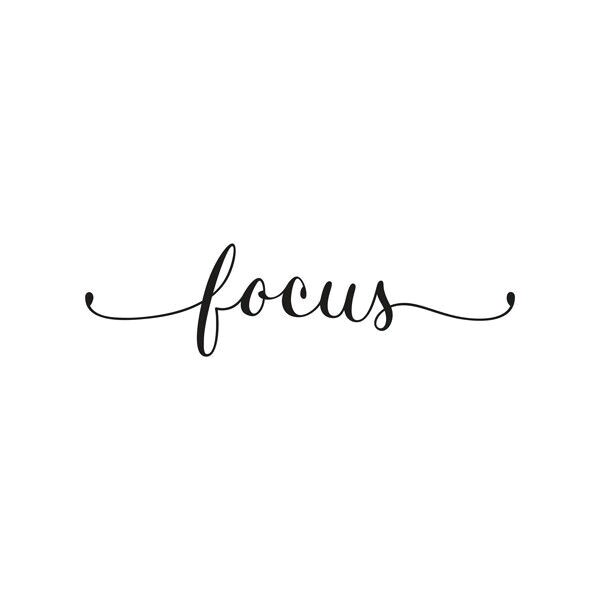
写得好好,文字干净又质朴,想起当年和友友一起在江汉路行走的时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