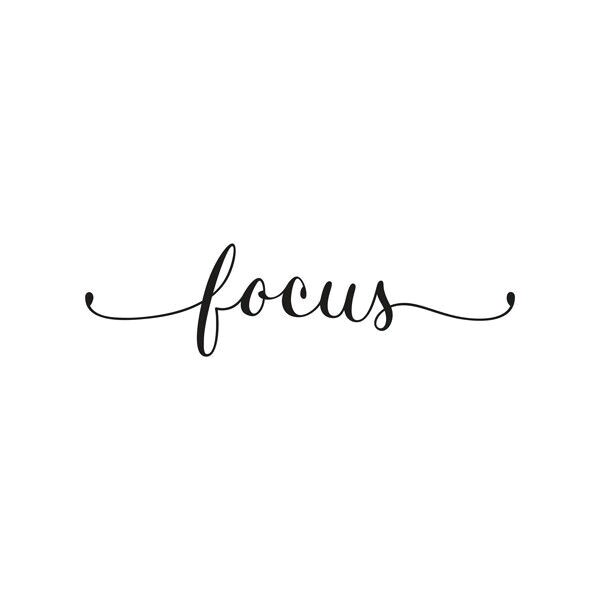让故事停下来,让思想往前走:这是博尔赫斯的衣钵。
麦家 《风声》代跋(关于《风声》的风声)
这个寒假在家闲着时和外婆一起看了电视剧《风声》,很惊喜。因为相比于电影,电视剧版本的改编其实是更贴合原著的;然后文咏珊的表演也让李宁玉这个我喜爱的角色更立体了。在这样的契机下,也顺带重读了一下麦家的《风声》原著。这次读的是微信读书里收录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版本,该版本在书的结尾收录了麦家和何平教授的对话,作为代跋。在这篇题为《关于<风声>的风声》的对谈纪实里,麦家阐述了自己的一些创作观,聊到先锋主义和博尔赫斯,也聊到当代小说和文学消费。其中有些观点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思考的匣子。之前当代文学还有文学理论课堂上想过的一些问题又重新冒出头来,促使着我又开始寻找答案。
大概还是本科的时候,果麦出了罗伯特·麦基的一套书,套装两本,分别是《故事》和《对白》。我当时在kindle上买了《故事》的电子书,后来也买了《对白》的实体书,这两本书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这两本书于我的意义,就是为我打开了理解“文学创作”或“语言艺术创作”的大门。小说的核心是故事,剧本的核心是对白。所以《故事》的核心思想似乎是告诉读者如何写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而《对白》的核心思想则似乎是告诉读者如何设计引人入胜的对白。
我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去阅读这两本书,里面有不少概念生涩难懂。或许我无法通过学习成为优秀的小说家或剧作家,但也正是基于这样“看教科书式”的阅读,让我从中领悟了一件事,那就是文学对于读者的意义绝不仅仅式沉浸与共情,应该还有思考与启迪。当读者尝试在文本中与作者对话的时候,那应该是他们思想交锋的时候。《对白》的序言中有这么一句话,似乎能概括我的所思所想:“时间过去,滔滔不绝的话语折损言语中的深意,因岁月冲刷而稀释的意义,又被故事浓缩。”
当我们被语言的魔术吸引,在叙事的迷宫中眩晕的时候,可曾试图发现作者埋下的草蛇灰线,指引我们领悟故事之外的深意。创作者在文学中创造故事和对白,出神入化地用真实的细节丰满了一个个虚构的形象。面对这些形象,我们理所应当地听得见它们的脚步声,可我们是否也能听见它们的心跳声?麦家在他的小说中,尝试为读者创造这样的机会。
《风声》就是这样一部初读可能会困惑,但再读便会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快感,这种快感应该源自于分析、比较与思考。在代跋中,何平教授引述了麦家在《风声》发表后当年获得年度小说家的颁奖词,此处我也引之:
麦家的小说是叙事的迷宫,也是人类意志的悲歌;他的写作既是在求证一种人性的可能性,也是在重温一种英雄哲学。他凭借丰盛的想象、坚固的逻辑,以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线索,塑造、表现了一个人如何在信念的重压下,在内心的旷野里为自己的命运和职责有所行动、承担甚至牺牲。他出版于二○○七年度的长篇小说《风声》,以从容的写作耐心,强大的叙事说服力,为这个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加冕,以书写雄浑的人生对抗精神的溃败,以关注他人的痛苦扩展经验的边界,以确信反对虚无,以智慧校正人心,并以提问和怀疑的方式,为小说繁复的谜底获得最终解答布下了绵密的注脚。麦家独树一帜的写作,为恢复小说的写作难度和专业精神、理解灵魂不可思议的力量敞开了广阔的空间。
麦家 《风声》代跋(关于《风声》的风声)
整部小说分为“东风”、“西风”和“静风”三部,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视角为我们还原了故事的历史现场。在东风篇,读者会为李宁玉的机警和智慧赞叹,对她的信仰和牺牲致敬,那种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是我们所读故事中最为司空见惯的理想光辉;但到了西风篇,顾小梦(电视剧叫顾晓梦)叙述版本的李宁玉形象却变成了一个几近歇斯底里的“疯子”,读者看到一个革命战士的惶惑与无助,一个站在阴影里的地下工作者如何为了任务而委屈求全;再到静风篇,作者借“我”所查阅的史料,为读者建构了旁支人物的身世故事,在这些线索中,读者可能会开始思考那可能并不存在的真相其背后的深意——我想那可能是在那个时代无法磨灭的理想主义者的光芒。不同篇章呈现了人物不同的人格切面,当我们能够将不同的声音整合到一起时,我们心中的“历史真相”也就原原本本地展于目前。或许这个真相不够美好,甚至有些黑暗,但真相背后的人性光辉却一定不会褪色。因为,在我看来深刻并不由赞歌称颂,而是来源于思考的淬炼,而后者也正应该是文学所擅长的。正如麦家自己所说:“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跟历史书对着干,这是文学的任务之一。”
书中除了李宁玉这个人物,值得说道的还有肥原。电视剧改编让我有点惊喜的地方也在于对肥原(电视剧叫龙川)的改编。在静风篇的最后一章,作者花了一些笔墨去写肥原的故事,尝试尽可能客观地为读者呈现一个生长在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青年,如何一点点转变成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这一篇作者借用了芥川龙之介和他在中国的故事来增加肥原故事的可信度,我想也算是一种致敬(《风声》的写法很难不让人想到芥川先生的《罗生门》和《竹林中》)。当他和芥川先生一起行走中国,看到因战火而伤痕累累的土地,他没有反思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而是在思考为何史书中的汉唐气象、天朝上国如今却如此不堪一击。他想扮演救世主,最终走向了和他所崇敬的芥川先生不同的道路。肥原身上呈现的诸多矛盾可能让他并不具有他所处群体(指日本军人)的代表性。但在我看来,肥原事迹所勾勒出的形象,正代表了那个动乱年代下,缺失信仰、被权力和欲望裹挟的知识分子,他们狭隘地解构文化,谄媚地迎合权力,他们或许清醒且有意志,但选择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也许他们在时代的洪流里翻腾起一点水花,却也终归被埋没于历史的尘土。
在这里,抛却对理想主义人格的赞颂,我思考更多的是史观问题——不管麦家本人写作时有没有这种考虑。这些年来,我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的史观能称得上人民史观,有些定义强调人民视角,有些定义强调人民立场。但细细思索可能会发现一个悖论,那就是谁能代表人民,谁的视角才算人民的视角,谁的立场才算人民的立场?对于这个问题,通过再读《风声》,我有了一些思路,但也不一定全对。我想其中的关键,应当在于实践。从书上看不到人民的视角,只能看到写书人的视角;从书上也读不出人民的立场,只能洞悉写书人的立场;只有实践,去看我们能看到的真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思考、分辨与体验,用智慧赋予或许荒诞的真实以自洽的逻辑,最后抽象出的答案或许才最接近历史本身。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开始重新审视文化、历史和记忆三者在历史语境下内涵的区别;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重读杜甫的诗歌时,才真正感受到这位诗人于中国文化史的伟大之处。
以上这些,我想都是《风声》故事之外带给我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本身,我认为特别有意义。有同样意义的还有对影视互动游戏《隐形守护者》二周目通关的思考,但这里就不再展开了。当代先锋主义小说家开始尝试全新叙事方式的时候,是不是想继承博尔赫斯的衣钵,我不知道。但是作为读者,我愿意去追寻故事之外的深意,我想这一定也是作家所希望看到的。当我们在小说文本中抽丝剥茧,从人物大开大合、大悲大喜的经验中走出来,回到最为普通、世俗的生活现场的时候,一旦把握住那些光怪陆离的文学形象背后的典型性,我想我们也能成为小说故事之外的“捕风人”。
最后以电视剧《风声》中,出自顾晓梦之口的一句话作结,我觉得甚好: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被流传,然而所有的故事终将被遗忘。水中火,火中冰,笼中兽,枕边刀,一切都是那么疯狂,然而最疯狂的还是时间,时间让一切轻易地飘散,就像短暂的,一啸而过的风声。
电视剧《风声》
后记:
这篇文章拖了很久。写这个主题的冲动最早源自于去年十一《隐形守护者》的二周目通关,后面寒假重读《风声》之后又有了新的思考。与其说是书评,更像是读书笔记吧。毕竟读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读法,大家各自的体会肯定也各不相同。我自己最深刻的阅读体验还是在阅读过程中对自己阅读经验的这种元认知,这个过程或许很漫长,这也是我拖延并想记录下来的原因。
最后放一张李宁玉的剧照,毕竟谁会不爱玉姐呢?